|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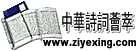 |
《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 |
|
──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
文/张帆 原载《历史研究》 2005年3期 子夜星网站整理收录
| |
|
【内容提要】许衡和刘因是元朝前期北方两大理学名儒,但二人的关系却有些微妙。刘因有一篇文章《退斋记》,不点名地严厉批评当时政坛上的一位大人物,一些学者猜测其批评对象就是许衡,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实际上,《退斋记》确系影射许衡之作。许衡在元初政坛屡出屡退,《退斋记》对他的批评有一定根据;但《退斋记》将许衡的行为指斥为“老氏之术”、“以术欺世”,则是求之过深,责之过苛,反映出刘因对许衡怀有很强的误解和成见。这种误解和成见,又与刘因个人的经历、性格、思想有着密切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朝统治下汉族儒士生不逢时的悲剧命运。 |
| |
|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谥文正)和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谥文靖)是元朝前期北方的两大理学名儒,在当时思想界具有重要影响,“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1]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末年,许、刘二人已被相提并论,刘因被评价为“自鲁斋之后,其道业、学术,未见出其右者”。[2]再晚一些,更出现了“覃怀许文正公衡进而师于上,保定刘征君因退而师于下”[3]之类说法,并有具体分析指出:“文正公被遇世祖,征居相位,典教成均,而门人贵游往往仕至显官。文靖公既出既归,学者多穷而在下,传其师说,私淑诸人。两公之门虽出处穷达有所不同,其明道术以正人心盖未始不一也。”[4]不过,许、刘两人之间的关系却有些微妙,不仅未见往来,也几乎没有互相提到过。许衡年长四十岁,对隐居乡里、名位不显的后生晚辈刘因不甚了解,未予称引,或是情理中事。但现存刘因著述,对声名显赫的前辈许衡也基本上从未正面提及,[5]直若不知世间有此人,就有些不寻常了。更有甚者,刘因有一篇文章《退斋记》被认为是专门影射许衡的,由此引发了后人对许、刘二人出处进退的种种评论。这篇文章的内容和写作背景,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刘二人出处进退问题,都很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近年以来,研究古代士人心态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有关“元代文人心态”就相继出版了两本专著,[6]还有为数颇多的文章。本文或可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
许衡、刘因二人皆有文集传世,然版本不一,卷数、篇目及分卷颇有异同。本文所用二人文集的版本,均取自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其中,许衡文集为《丛刊》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刊十四卷本《鲁斋遗书》,刘因文集为《丛刊》影印明成化十五年蜀藩刻二十八卷本《刘文靖公文集》。
一、刘因《退斋记》确系影射许衡之作
首先要讨论《退斋记》的问题。《退斋记》载于《刘文靖公文集》卷一八,[7]是刘因在至元十三年(1276)八月十六日为友人滕安上所作。滕安上(1242—1295),字仲礼,中山安喜(今河北定县)人。以“退斋”名居室,约刘因作记。刘因在文中就进退之义大发议论,严厉批评了一种欲进先退、以退为进、隐含深刻心计权谋的“老氏之术”。文章开篇从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道”谈起:
老氏其知道之体乎?道之体本静,出物而不出于物,制物而不为物所制,以一制万,变而不变者也。以理之相对、势之相寻、数之相为流易者而观之,则凡事物之肖夫道之体者,皆洒然而无所累,变通而不可穷也。彼老氏则实见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见夫此也。
接下来笔锋一转,罗列道家人生观的种种表现,语言尖刻,尽显贬义:
虽然,惟其窃是以济其术而自利,则有以害夫吾之义也。下,将以上也。后,将以先也。止,将以富也。俭,将以广也。哀,将以胜也。慈,将以勇也。不足,将以无损也。不敢,将以求活也。无私,将以成其私也。不大,将以全其大也。柔弱,将以不为物所胜也。不自贵,将以贵也。无以生,将以生也。知洼必盈,于是乎洼。知弊必新,于是乎弊。知少必得,于是乎少。知朴素之可以文,于是乎为朴素。知溪谷之可以受,于是乎为溪谷。知皦之势必污,盈之势必溢,锐之势必折,于是乎为婴儿,为处子,为昏闷晦寂。曰忿、曰武、曰争、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阉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辩而示之讷,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荣而示之辱。虽出一言,而不令尽其言,事则未极而先止也。故开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终,皆捭焉而不与,而置己于可以先、可以后、可以上、可以下、可以进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终,未入而图其出,据会而要其归,阅衅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见其迹焉。虽天地之相荡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测者,亦莫不在其术中,而况于人乎?故欲亲而不得亲,欲疏而不得疏,欲贵而不得贵,欲贱而不得贱,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关键橐钥不可窥而知,其机纽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以形象而抟执也。
到此为止,基本上是洋洋洒洒的泛论。再下面明显就是带有针对性的指斥了:
呜呼!挟是术以往,则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节量天下之休戚,其终必至于误国而害民,然而特立于万物之表而不受其责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时义、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夺之也。
文章最后以勉励滕安上收尾,希望他“不为老氏之退”,“慎其所以退”,“非如为老氏者之以术欺世、而以术自免者也”。
这篇文章在元代较有知名度,也可以说是刘因的一篇名作。元朝后期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就收录了此文。[8]一般以为,此文后半段的影射对象“彼”,就是指许衡。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在其《题许文正公集后》、《书刘文靖公退斋记后》两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9]相关论述又被转引到《宋元学案》卷九○《鲁斋学案》和卷九一《静修学案》中,更加扩大了影响。但总的来说,全祖望的具体论证并不是很充分,因此有的学者谈到这件事时仍持怀疑态度。杜维明即认为,《退斋记》影射许衡的说法是难以确证的。[10]学术界迄今为止最详尽的刘因研究专著、商聚德《刘因评传》一书,也不同意全祖望的观点。[11]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全祖望的看法无误,《退斋记》确系影射许衡之作。
先看一下全祖望的论据。全氏的论据共有两条,都引自元人著述。一是杨俊民《静修先生祠堂记》。杨俊民,字士杰,真定人,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进士,官至国子祭酒。他曾受学于刘因的私淑弟子安熙(1270—1311),因此对刘因十分尊崇。所撰《祠堂记》,见载于《刘文靖公文集》卷二七《附录上》。[12]其中有云:
先正得时行道,大阐文风,众人宗之如伊、洛。先生(引者按:指刘因)斥之曰:“老氏之术也。”详具《退斋记》。
杨俊民所说的“先正”是否即指许衡?商聚德《刘因评传》就此辩解说:“在元初,‘得时行道、大阐文风’的大有人在,怎么能一定说是指许衡呢?”但是,如果结合“众人宗之如伊、洛”一语来看,在元初思想界具有“伊、洛”地位的,除许衡外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人。全祖望的另一条论据是虞集《安敬仲文集序》。虞集(1272—1348),字伯生,侨寓抚州崇仁(今属江西)的蜀人,元朝后期文坛领袖,是南方理学大儒吴澄的学生,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其年辈要比杨俊民长一些。安敬仲,是安熙的字。虞集此序见载于其文集《道园学古录》卷六,又被苏天爵收入《国朝文类》卷三五(题为《安先生文集序》)。[13]这篇序虽然是为安熙文集所作,却有大段篇幅谈到刘因。其中说(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昔者天下方一,朔南会同,缙绅先生固有得朱子之书、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细矣。而静修之言曰:“老氏者,以术欺世而自免者也。阴用其说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节量天下之休戚,其终必至于误国而害民,然而特立于万物之表而不受其责焉。而自以孔孟之时义、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夺之也。”观其考察于异端几微之辨,其精如此。
虞集所引“静修之言”,当然是出自《退斋记》。他认为《退斋记》的影射对象是一位“得朱子之书、而尊信表章之”,使得朱熹学说“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的“缙绅先生”,验诸史实,这实在只差说出许衡的名字了。事实上,在其他文章中,虞集正是用几乎同样的话来正面描述许衡。《国朝文类》卷三○虞集《张氏新茔记》:
许文正公衡,生乎戎马抢攘之间,学于文献散逸之后,一旦得其(引者按:指朱熹)书而尊信之,凡所以处己致君者,无一不取于此。而朱子之书遂衣被海内,其功讵可量哉![14]
《道园学古录》卷三六《南康路都昌县重修儒学记》:
世祖皇帝时,许文正公实得朱子之书而表章之,而其言遂衣被于天下。[15]
两相比较,前文的“缙绅先生”就是许衡,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只不过由于许衡在元代的特殊地位,在谈到其受批评、被攻击时,为贤者讳,隐去姓名而已。[16]杨俊民所说“先正”,应当也是相同的情况。
实际上,全祖望没有注意到,关于《退斋记》影射许衡一事,在刘因著述中可以找到一条内证。这就是另一篇文章《蠢斋说》:
近世士大夫多以顽钝椎鲁、人所不足之称以自号。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为是谦托而然也,盖必有所取焉耳。然其所取之义有二焉。盖或病夫便儇狡厉之去道甚远也,思欲自矫以近本实,于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与其失于彼也,宁失于是。此其设心,于义为无所失也。或为老庄氏之说者则不然,以为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后可以无营而近道、保啬而自全也。此则择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则将以自利而已。使前之说行,亦不过人人尚质,而于世固不为无益也。若不幸而此说一炽,则天下之人皆将苟简避事,而其为害,庸有既乎?呜呼!一事之间,心术之微,其义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之察也。[17]
本文写作年代不明,写作原因则与《退斋记》完全相同,即为友人屋宇作题记。文章最后提到“蠢斋”的主人是安肃(今河北徐水)人刘仲祥,其具体事迹已不可考。但很明显的一点是,文章中的议论并非针对刘仲祥,而是别有所指。其批评对象,也与《退斋记》大体一致,即在“老庄氏”道家人生观影响下的“保啬而自全”、“苟简避事”一类自利行为及其所含“心术之微”。具体人物,当然就出在“以顽钝椎鲁、人所不足之称以自号”的“近世士大夫”之中了。我们不清楚元初士人是不是有取“顽斋”、“钝斋”、“椎斋”别号的,但知道的确有一个人别号“鲁斋”,那正是许衡。[18]刘因又有《蠢斋》诗:
莫倚蠢愚遂自疏,保身须要畏刑书。头边既有儒冠在,谁为斋名赦得渠?[19]
这首诗应当仍是为刘仲祥所题,但诗中的嘲讽对象、第三人称“渠”,不大可能是刘仲祥。相信此诗仍然是借题发挥,仍然是影射以“顽钝椎鲁”之称为斋名的鲁斋先生许衡。
全祖望《书刘文靖公退斋记后》分析《退斋记》的写作背景说:“岂当日文正(许衡)辞左辖,居祭酒,盖有见于道之难行,而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刘因)以是诋之欤?……由文靖之言观之,则知苟非行道之时,必不当出,亦不当择地而居之。盖立人之朝,即当行道,不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间而明道之为愈也。”按许衡辞去中书左丞职务,改任国子祭酒,事在至元八年(1271)三月,而《退斋记》的写作时间,如前所述,则在至元十三年八月十六日,相隔将近五年半。如果说刘因对许衡五年半以前的行为念念不忘,耿耿于怀,作文追诋,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我相信《退斋记》中滔滔不绝的议论更像是因近事而发。什么近事呢?那就是至元十三年七月,许衡从家乡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应诏复出,入都参加历法制订工作。此时刘因正在保定容城(今属河北)家中,距大都至河南的驿道很近。朝廷使臣南下征召许衡,许衡奉诏北上,这些消息刘因很快就会知道。他或许对元廷征召许衡的目的并不完全了解,但无论如何,许衡是在归隐后复出了,而且此前即曾屡次归隐,屡次复出(对此下文另述)。在刘因看来,这实在是典型的“老氏之退”,属于“以术欺世”,遂有《退斋记》中激昂慷慨的大段批评。因此,全祖望对《退斋记》写作背景的推测,恐怕不尽准确。不过当至元八年许衡“辞左辖,居祭酒”之时,劝说许衡彻底归隐、“居田间而明道”的也确有其人,此人是东平(今属山东)人王旭。王旭,字景初,生卒年不详,成宗大德时尚在世。《国朝文类》卷三七载有王旭《上许鲁斋先生书》,[20]开篇称“三月朔日,东平晚进王旭谨斋沐裁书,顿首百拜,献于左丞先生阁下”。信中先谈了一番作者对“道学”(即理学)的理解,感叹道学尚未被士人普遍接受,“文风不振,士气卑陋”,“正道不明,士习乖僻”,随之对许衡提出大段规谏:
伏惟先生以道鸣世,践履于平昔者,皆三才之实学,发挥于事业者,皆三才之实用。箪瓢居陋巷,浩然无一毫之不足,白衣登相府,淡然无一毫之有余。其尧舜吾君、成康吾民,盖胸中之素蕴。一谏不行,奉身而退,其出处进退,何其一于义而不苟、伸于道而不屈也!吾道有光,士气増重,其颓波之砥柱、冥途之日月与?虽然,仆固以圣贤望先生,而不以世俗之所以待者待先生也,则犹不能无疑。何者?孟子致齐卿之位,齐王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而孟子不可,以为辞十万而受万。而先生之所以眷焉于此者,其必有以处此矣,而旭也未闻其说焉。何如返苏门之故隐,卧西山之白云,远续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圣传不坠,后学有归?旭也不敏,请抠衣执笔,以书先生于文公(引者按:指朱熹)之后。狂言区区,唯先生怜其心,而略其愚妄之罪以进之。幸甚!
据《元史》卷七《世祖纪四》,许衡解除左丞职务、改任国子祭酒的命令,发布于至元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乙酉)。王旭的书信,则写于三月初一日。大约此时许衡已有“辞左辖,居祭酒”的打算,或是朝廷已有如此安排,仅尚未正式颁布而已。所以王旭既称许衡为“左丞先生”,又说他“一谏不行,奉身而退”。但在王旭看来,许衡“退”得显然不够彻底,因此自己“犹不能无疑”。他随即引用了《孟子·公孙丑下》记载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孟子辞去齐卿之位打算回家,齐王提出挽留方案,在国都中给孟子一间房屋,用万钟之禄养活他的门徒,“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予以拒绝,说:如果我想发财,何必辞去齐卿的十万钟俸禄而接受这区区一万钟的赐予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四就此解释说:“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则其义不可以复留,……又有难显言者,故但言设使我欲富,则我前日为卿,尝辞十万之禄。今乃受此万钟之馈,是我虽欲富,亦不为此也。”[21]王旭引用这个故事来规谏许衡,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对《四书集注》“敬信如神明”[22]的许衡,一眼就会看出其中寓意。在王旭看来,许衡与孟子状况一样,也是“既以道不行而去,则其义不可以复留”,不理解他为什么仍然“眷焉于此”,建议他“返苏门之故隐,卧西山之白云”,彻底与政治划清界限。当然,如我们所知,许衡并没有接受王旭的建议,而是接着做了三年国子祭酒,因办学经费不继,方于至元十年辞官回乡。之所以征引王旭的这封书信,是因为联系起来看,它使我们更易于理解刘因《退斋记》的内容,更加相信《退斋记》是影射许衡之作。二文写作时间虽相隔近五年半,但论述内容都是理学家的出处进退问题,只不过王旭是对许衡正面规谏,刘因是对许衡侧面攻击而已。[23]
顺便还应指出,《退斋记》影射许衡之说,并非全祖望独具慧眼的发明。在元代,许衡地位特殊,因此虞集、杨俊民谈到《退斋记》,只能作出闪烁其词的暗示。而到明代,许衡不再是“本朝儒宗”,学者谈到他受刘因攻击一事,就没什么顾忌了。明中期学者罗钦顺评论说:“刘静修之讥许鲁斋,颇伤于刻。”[24]虽未明言,但所指肯定是《退斋记》,至少包括《退斋记》在内。有趣的是,发生在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断绝了著名才子唐伯虎(唐寅)功名之途的一次科场案,竟然也与《退斋记》有直接关系。这一年科举会试结束后,言官弹劾主考程敏政向举人徐经、唐寅泄露试题,程敏政被迫致仕,愤恨而卒,徐经、唐寅黜充吏役。据徐经招供,此前他与唐寅问学于程敏政,讨论到科举第三场策论可出的一些题目,因而与唐寅拟作文字,流传于外。不料程敏政果真被点为会试考官,所出策论题中含有他们以前讨论过的题目,遂被怀疑“卖题”,实则并非事先有意泄露。[25]当时引发攻讦的策论题是这样的:
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则无所据以得师,而为归宿之地矣。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者,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后学亦徒因古人之成说谓其尔,然真知其似伯夷、似展季、疑于禅、疑于老者,果何在耶?请极论之,以观平日之所尝究心者。[26]
据时人陈洪谟分析,这道题的难点就在于“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一句。而此句所指实为许衡,其用典“出刘静修《退斋记》,士子多不通晓”。[27]这样一道难题,徐经、唐寅事先拟作,自然有作弊嫌疑了。明末查继佐谈到此事时明确认为:“贿题……许鲁斋一段,出刘静修《退斋记》,通场莫解,独经与寅合式,属敏政消息无疑。”[28]此案真情暂置不论,它至少告诉我们,《退斋记》影射许衡一事,明代有一些博学的读书人是了解的。当然了解的人很少[29],否则不会“通场莫解”,并且引发攻讦。总之,《退斋记》确为影射许衡而作,这一点元人很清楚,但碍于许衡的地位,不便明言。明代仍有学者了解此事。到全祖望,只是明确加以阐述而已。
二、许衡的出处进退
初看许衡的履历,我们会发现,《退斋记》对他的批评不无根据。许衡始入仕途,是在四十六岁时即蒙古宪宗四年(1254),被征为京兆(今陕西西安)教授。京兆是忽必烈的分地。次年,忽必烈的近臣畏兀儿人廉希宪宣抚关中,推荐许衡为京兆提学,许衡坚辞不受。宪宗八年,离任返家。这五年的教授生涯,严格说来算不上从政,但却是许衡与忽必烈产生联系的开端。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汗位,寻即征召许衡入朝,自此许衡开始了他在政坛上的“屡进屡退”。据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从这一年直到许衡去世的前一年至元十七年(1280),二十年间,许衡凡五度在朝,五次归隐。简况如下:
第一次在朝:中统元年五月,应召北上。二年九月,以疾辞归老家怀孟。
第二次在朝:中统三年(1263)九月,应召北上。至元元年(1264)正月,辞归。
第三次在朝:至元二年十月,应召北上,奉诏入中书省议事。四年正月,辞归。
第四次在朝:至元四年十一月,应召北上。六年,参与更定官制。七年正月,拜中书左丞。八年三月,改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十年七月,辞归。此次在朝近六年,是许衡在朝时间最长的一次,随后家居三年,也是中统元年以来他在家时间最长的一次。
第五次在朝:至元十三年七月,应召北上修历。十五年三月,授集贤大学士兼教领太史院事。十七年春,历成。八月,辞归。次年三月去世。
可见,“屡进屡退”的确是许衡政治生涯的主要特征。[30]许衡去世后,翰林学士承旨王磐为作画像赞,将许衡形容为忽而“躬耕太行之麓”,忽而“判事中书之堂”的高人,说他“随时屈伸,与道翱翔”,“布褐蓬茅,不为荒凉;珪组轩冕,不为辉光”。[31]元末欧阳玄奉诏为许衡作代表官方观点的神道碑,也指出他“君召辄往、进辄思退”的特点。[32]明儒薛瑄则评论许衡“视富贵如浮云”、“去就从容”,谓其“召之未尝不往,往则未尝不辞”是“善学孔子者也”。[33]以上都是正面的评价。但换个角度看,这种“君召辄往、进辄思退”、忽进忽退、半进半退的政治态度,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正面理解的,因此才会有王旭的规谏和刘因的批评。许衡晚年曾忏悔说:“我生平为虚名所累,竟不能辞官。”要求家人在他死后“慎勿请谥、立碑,必不可也,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令子孙识其处足矣”。[34]可见《退斋记》一类负面议论对许衡造成的心理压力并不算小。
那么,许衡为什么会有屡进屡退之举呢?果真如《退斋记》所言,是“济其术而自利”、“以术欺世”的道家处世方式吗?
作为一个士人和理学家,许衡对政治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度有十分乐观的行道用世理想。《鲁斋遗书》卷一一《赠窦先生行二首》之二:
莫厌风沙老不禁,斯民久已渇商霖!愿推往古明伦学,用沃吾君济世心。甫治看将变长治,呻吟亦复化讴吟。千年际会真难得,好要先生着意深。[35]
窦先生即许衡的好友窦默(1196—1280),他于蒙古海迷失后元年(1249)被忽必烈聘入幕府,许衡的送别诗应当就作于此时。[36]在大蒙古国统治下,汉地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士大夫只能寄希望于忽必烈这样的“贤王”,许衡写出上面的诗不算奇怪。然而当五年之后他被忽必烈聘为京兆教授时,或许是出于理学家的矜持,却百般推辞。[37]任教授后,廉希宪推荐他为京兆提学,他又以不谙“举业”坚拒。[38]中统元年,忽必烈刚刚即位,即召许衡入朝,按说此时许衡的“千年际会”已经来临,他大可努力实现“推往古明伦学”、“沃吾君济世心”的理想。但是,许衡很快体会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忽必烈对“汉法”的推行,是不彻底和有保留的;对士人的重用,也明显倾向于王文统一类“尚霸术、要近利”[39]的人物。窦默在觐见忽必烈时面斥王文统“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忽必烈问谁可为相,窦默说:“以臣观之,无如许衡。”忽必烈“不怿而罢”。[40]在这种情况下,许衡难在朝中立足,不久遂辞职返乡。此后他几度复出,参与了一些制度创建工作,但总体来说,对政局的悲观失望情绪有增无减。王文统虽以涉嫌谋反被诛,但忽必烈又开始重用回回敛财之臣阿合马,对儒臣日渐疏远。至元三年,许衡第三次在朝期间,向忽必烈呈上了著名奏疏《时务五事》。奏疏批评汉化改革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岁计不足”,“无一定之论”,并对元朝汉化进程作了比较悲观的估计,认为“非三十年不可成功”。[41]在给窦默的一封辞荐信中,许衡写道:
老病侵寻,归心急迫,思所以上请,未得其门也。迩来相从,实望见敎,不意复有引荐之言,闻之踧踖,且惊且惧。……治非一日之为也,其来有素矣。……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时也,时之所向势也。势不可为,时不可犯。……或者横加己意,欲先天而开之,拂时而举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斫也。揠苗则害稼,代匠则伤手。是岂成己成物之道哉?……今先生直欲以助长之力,挤之伤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为耶?[42]
此信写作年代不详,但从开篇“老病侵寻,归心急迫”一语来看,应当是作于某次辞职返乡前夕。同样是写给窦默,昔日“甫治看将变长治,呻吟亦复化讴吟”的乐观思想,此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前后情绪变化,真有云泥之别。
许衡在朝情绪悲观,除对政局失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忽必烈对他始终不甚赏识。由于许衡身后地位的抬高,他与忽必烈的“君臣遇合之契”往往被元人夸大[43]。实际上,在忽必烈即位前搜罗的“潜邸旧侣”中,许衡只是一个外围或边缘成员,地位明显不及他的好友姚枢和窦默,更远不如刘秉忠一类权谋术艺型人物。这段时间许衡是否见过忽必烈,都是值得怀疑的[44]。《考岁略》记载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后召见许衡,询问其“所学”、“所长”、“所能”,完全像是初次见面的谈话。又载当时王文统秉政,“深忌雪斋(按指姚枢)诸公,以先生素无因缘而弗惮也”。“素无因缘”一语,颇能反映许衡在忽必烈“潜邸”集团中的地位。至元三年二月,许衡第三次在朝期间,复获忽必烈召见,“面奉德音”。《考岁略》记载“德音”的内容,有云“人皆誉汝,想有其实”,又云“谓汝年老未为老,谓汝年小不为小,正当黾勉从事,毋负汝平生所学”。言语颇乏礼貌,而且表明此时忽必烈对许衡仍然不甚了解,只是从其他人那里听到对许衡的称誉之词,处于将信将疑之中。此后近一年内,许衡与忽必烈接触较多,“屡蒙访问”,奏疏《时务五事》即上于此时。后来第四次入朝,参定官制,进拜中书左丞,为许衡一生政治事业的顶点。但即使此时,许衡仍未真正感受到忽必烈的知遇。他推辞左丞职务说:“臣之所学迂远,与陛下圣谟神算未尽吻合。陛下知臣未尽,信臣未至,直以虚名误蒙采擢。”[45]虽当时辞呈未准,但左丞只做了一年多,终于辞政从教。君臣意见“未尽吻合”的原因,主要是忽必烈在政治上功利思想浓厚,“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天性,终其身未尝少变”,[46]对理学家的道德性命之说,视为迂腐,不予重视,甚至并不理解。[47]而许衡所长、及其为时人所重,恰恰在后一方面。《考岁略》说他“每入奏对,以格君心为已任”。魏初《许左丞哀挽》诗序:
至元戊辰(引者按:至元四年),尝从先生入京。见先生敷奏,如学知生知之说、人心道心之论,皆款曲至到。虽承诘问,辞气自如。[48]
胡祗遹《挽许左丞鲁斋》:
忆昔朝廷求直言,奇谟伟画争后先。对病之药不易得,大策与众殊相悬。不从事事论得失,清流莫若先澄源。曰心曰性阐圣学,敷陈详悉登经筵。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心一片金石坚。当年群儒那解此?迂阔讥议何绵绵。陶钧高志惜未遂,沁南养疾桑麻田。……[49]
许衡讨论问题“不从事事论得失”,而要“曰心曰性阐圣学”,大讲“学知生知之说、人心道心之论”。对此视为“迂阔”的恐怕不仅仅是“当年群儒”,首先是忽必烈本人。所以忽必烈后来会对许衡的学生、康里贵族不忽木说:“曩与许仲平论治,仲平不及汝远甚。先许仲平有隐于朕耶?抑汝之贤过于师耶?”[50]
既然如此,屡退之后为何又会屡进?首先需要指出,忽必烈虽对许衡不甚欣赏,但由于他名气较大,并且为人耿直(这一点下面还要提到),也不愿与其过分疏远,仍希望让他发挥一些作用。在忽必烈看来,许衡在具体政见上虽然迂阔,但他讲的纲常伦理之道,仍有很大利用价值。据称忽必烈“雅知崇尚《四书》”,并曾对侍臣说:“孔子之道,三纲也,五常也。彼缀辑诗赋者,皆为伪耳。”[51]这大约多少是受到了许衡的影响,至少表明两人之间有一定的共同语言。因此许衡每次退隐后,忽必烈又总是遣使前去征召。而在许衡一方,自从受聘担任京兆教授起,即与忽必烈确立了君臣名分。他对忽必烈和蒙古政权的忠诚,此后从未动摇。许衡为人平易,从政态度也有务实的一面。他曾说:“舍苗不耘,固为有害,助而揠之,其害甚大。”[52]虽以“得君行道”为理想,但如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也不妨做一些客观条件允许、力所能及的工作,故又称:“君子于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之间,惟为其所当为,随其身之所寓,坦然安舒,无所入而不自得。”[53]薛瑄评价许衡“盖真知实践者也”。何瑭则总结他“学以躬行为急,而不徒事于言语文字之间;道以致用为先,而不徒急乎性命之奥”。[54]唯其强调“实践”,所以不轻易放弃“躬行”、“致用”的机会。至元八年辞政从教时,即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说:“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55]此时他已年逾花甲,却每天居于学中,“朝夕莅事,略无老人疲倦之意”。[56]在这种心态下,对于王旭“辞十万而受万”的批评,自然是听不进去了。至元十三年家居被召,是因为忽必烈要制定历法,许衡以能“明历理”得到张文谦、张易、王恂、郭守敬诸人合辞推荐。在许衡看来,制定历法当然是国家大事,因此不辞劳苦,力疾前往,不料却遭到了刘因《退斋记》的严厉抨击。
从史料中反映的情况看,许衡同时代人对他的人品,几乎是众口一致地赞誉。《考岁略》记载蒙古贵族、右丞相安童拜会许衡后,“心悦诚服,念念不释者累日”,对身边的人说:“若辈自谓相去几何?盖什百而千万也,是岂缯缴之可及耶!”又载著名文士王磐“襟宇盖世,少所许可,独敬礼先生(指许衡)”,与许衡谈话时每云:“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缩耳。”甚至反面人物阿合马在与许衡辩论时也说:“人所嗜好者势利爵禄声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这些话见于许衡学生笔下,自然有过誉之嫌,但似乎也不能视为完全编造。魏初挽诗云:“学道躬行意味真,爱君辞气见忠纯。千秋万古先贤传,合作中朝第一人。”[57]王恽作画像赞,称颂许衡是“屹倾波之砥柱”,“天下至诚”,“魁然真辅”。[58]《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王文肃公》引杨文郁《王恂墓志》:
公(王恂)……与人少许可,虽权贵未尝假以辞色,刚稜疾恶,至负高气以忤之。既与许公(许衡)同太史院,谓人曰:“先贤吾不得而见之,今得许公可矣。”渐磨之久,德宇为之一变。[59]
魏初、王恽、杨文郁都不是理学中人,他们的评价或记载,应当较有可信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许衡还以性格耿直为时人所称。忽必烈初即位时召其入都,就是窦默将他作为当代“魏征”推荐的结果[60]。王恽《论左丞许公退位奏状》:
伏见左丞许公衡,师心《大学》,养气至刚,独立危言,清苦自守,挺然有“蹇蹇匪躬”之操,方之古人,不可多得。且自立中省,迄今十有二年,前后相臣,如衡竭尽者多矣,未若许之切直敢言、不以荣贵为心者。[61]
《考岁略》形容许衡的辞官是“不肯枉尺直寻”,欧阳玄《许衡神道碑》也惋惜地说:“方世祖急于亲贤,而先生笃于信已,以是终无枉尺直寻之意。”按“枉尺直寻”一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意谓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八尺为一寻),比喻为了大有所获,不妨小有所屈。在《考岁略》、《神道碑》作者看来,许衡要是愿意“枉尺直寻”,圆滑一点,根本不必遭遇屡进屡退的坎坷。以上这些评价、描述,实在难以同《退斋记》所云“济其术而自利”、“以术欺世”的老氏之徒联系在一起。商聚德正是从这个角度反驳《退斋记》影射许衡的说法。他指出:“许衡的‘辞左辖、居祭酒’能说是老氏之术吗?恐怕不能。……许的为人是颇为廉直方正的,……并不贪恋高位,居官也是尽职尽责的,谈不到什么‘以术欺世’的问题。”[62]这段话大体无误,但由此认为《退斋记》的影射对象并非许衡,在逻辑上不足以成立。许衡没有“以术欺世”,并不能保证《退斋记》作者不会对他产生这一类误解。
总之,虽然许衡确有“屡进屡退”之举,《退斋记》所言似乎有据,但如果更具体细致地了解许衡其人其事,就会感到,《退斋记》的批评作为诛心之论,未免求之过深,责之过苛,如罗钦顺所言,“颇伤于刻”。[63]客观地讲,许衡的屡进屡退,主要反映出他在“忠君”与“明道”两大原则间的痛苦徘徊,很难说是权谋心术的表现。《考岁略》在总结许衡仕途经历时自信地说:“先生……于利名纷华,畏若探汤,诚心自然,天下信之。”但从《退斋记》来看,所谓“天下信之”,并未完全做到。尽管许衡也曾义正辞严地指责老子的学说“与吾儒全别”,“多隐伏退缩,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64]但他自己却终于未能逃脱“老氏之术”的批评。[65]这也可以算是许衡生平的一大遗憾了。
三、刘因的出处进退
《退斋记》一文认定许衡“以术欺世”。这方面的误解和成见,与作者刘因个人的经历、性格、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刘因幼有异禀,是一位神童。苏天爵《刘因墓表》记载说:“先生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随目所见,皆能成诵。六岁能诗,十岁能属文,落笔惊人。”[66]他年轻时曾从南宋儒生砚弥坚受业[67],但后来的学术路径究竟受砚弥坚影响多大还不好断定,似乎更多地是自己摸索而致,故尝有诗称:“平生自恨无师友,千古空闻圯下风。”[68]《刘因墓表》则云:“先生年未弱冠,才气超卓,日阅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至元四年(1267)十九岁时,作《希圣解》一文,自称在梦中受到拙翁(按指周敦颐)、无名公(指邵雍)、诚明中子(指张载)的训导,因而立下了“希圣”、“希天”的志向[69],这是刘因理学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标志。此后讲学授徒,终成一代名儒。
学者已经注意到,尽管许衡、刘因并称元代北方理学两大代表人物,但二人的学术渊源不尽相同。许衡三十四岁时,获读程颐《易传》和朱熹的多种著作,由此改宗伊洛之学,治学“一以朱子之言为师”,[70]“嗜朱子学不啻饥渇,凡指示学者,一以朱子为主。或质以他说,则曰:‘贤且专主一家,则心不乱。’”[71]刘因则出生较晚,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相对安定,有机会广泛涉猎理学诸儒的著述。此时他年纪尚轻,学习、接受能力较强,加上天资聪颖,因此能够兼采诸家,自有去取。《元史》本传载:“及得周(敦颐)、程(颢、颐)、张(载)、邵(雍)、朱(熹)、吕(祖谦)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及评其学之所长,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其高见远识率类此。”[72]元末人赵汸云:
初,国家既收中原,许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书而尊信之。及事世祖皇帝,遂以其说教胄子,而后王降德之道复明。容城刘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张所尝论著,始超然有见于义理之当然、发于人心而不容己者。故其辨异端、辟邪说,皆真有所据,而非掇拾于前闻。出处进退之间,高风振于天下,而未尝决意于长往,则得之朱子者深矣![73]
也就是说,由于刘因能由朱学“上求周、邵、程、张”,因此才会“超然有见”,“真有所据”,“得之朱子者深”。袁桷也说:“保定刘先生因,笃志独行,取文公书会粹而甄别之,其文精而深,其识专以正。”[74]含义大体相同。这样,许、刘二人的学术造诣,就有了高下之分。许衡“得朱子数书于南北未通之日”[75],本未能窥朱学之全体,又没有做到兼采诸家,会粹甄别,故而“所业者不外《小学》、《四书》”,[76]论学缺乏深度和创造,以至被黄百家讥为“所见只具粗迹”。[77]刘因则在这方面一向受到较高评价。据《刘因墓表》记载,与刘因同岁但晚卒四十年的南方理学大儒吴澄,“于海内诸儒最慎许可”,惟对刘因“独知尊敬”。虞集则说:“予观于国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学者髙明坚勇,孰有过于静修者哉?诚使天假之年,逊志以优入,不然使得亲炙朱子,以极其变化充扩之妙,则所以发挥斯文者,当不止是哉!”[78]
刘因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后人谓其“俯视一世,藐焉不满,其风节孤峻,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79]。他曾经在自己的画像上写下这样的题辞:
所以承先世之统者,如是其孤;所以当众人之望者,如是其虚。呜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80]
刘因是其父四十多岁才生的独子,“承先世之统者如是其孤”当然主要应从这方面理解。不过联系到他对理学诸儒的“发微”品评,以及《希圣解》所载周敦颐等人对他“希圣”、“希天”的教诲,所谓“先世之统”恐怕多少也有道统的寓意在内。然而在当时北方大多数学者的眼中,承继理学道统的人却是年长位尊的许衡。刘因本来就“平生极罕许可”,[81]后人对刘、许学术造诣的不同评价,当时的人虽不一定都能体会到,但刘因自己肯定有着深切感受。因此他对于许衡,缺乏对前辈的尊敬和对同道的支持,相反却颇有鄙夷敌视之意。“朝廷别有真儒在,莫道斯文赖我扶!”[82]这样愤懑不平的诗句,应当主要是针对许衡的。传世刘因著述中几乎从未正面提到许衡,绝非偶然。而《退斋记》中对许衡的成见,也就易于解释了。
刘因很早就选择了不求仕进的隐居生活。《刘因墓表》云:“先生杜门授徒,深居简出,性不苟合,不妄接人。保定密迩京邑,公卿使过者众,闻先生名,往往来谒,先生多逊避不与相见。不知者或以为傲,先生弗恤也。”陶宗仪曾记载一个故事:中统元年许衡应召赴都,途中拜访刘因。刘因问:“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许衡回答:“不如此则道不行。”后来刘因一再拒聘,就此向人解释说:“不如此则道不尊。”[83]这是现存史料中唯一一条许、刘二人会面的记载,但可惜具体情节是不真实的。中统元年刘因不过十二岁,许衡不可能去专门拜访他(不仅此时不可能,后来许衡也不可能亲自登门拜访这位与自己素无渊源、又年轻四十岁的晚辈)。[84]不过,这个故事却反映了元人对许衡、刘因不同从政态度的理解。大约在刘因死后不久,已经有了“刘梦吉之高明,许鲁斋之践履,未易优劣”的评价,并且“四海传诵,以为名言”。[85]明人崔铣则说:“许鲁斋实行之儒,刘静修志道之儒。”[86]意思基本相同。作为“高明”的“志道之儒”,刘因对自己的进退出处看得很重,与强调“践履”的“实行之儒”许衡有明显区别。前文曾引述许衡的言论“舍苗不耘,固为有害,助而揠之,其害甚大”。刘因在这方面的的态度,则是若不能“助而揠之”,宁肯“舍苗不耘”。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就是“不有拨乱功,当乘浮海舟”。[87]况且由于刘因出生较晚,到他成年时,已经错过了忽必烈潜邸时期和即位之初儒臣受重用的黄金时代。面对“当国者急于功利,儒者之言弗获进用”[88]的时局,心高气傲的刘因自然不肯轻出。全祖望分析他“盖知元之不足有为也,其建国规模无可取者,故洁身而退,……睹时政之谬,而思晦迹以自保”。[89]大体上是不错的。以这种态度来看屡进屡退、仆仆奔走于道路的许衡,当然很难从正面理解,更何况刘因本来就对许衡没有好感。
另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写作《退斋记》之时),刘因的隐居态度并不是完全坚决。故而《退斋记》对许衡的批评,主要是指责他进退无恒,并没有说一定应退不应进。也正因如此,后来才会有至元十九年(1382)刘因的一度出仕。
刘因出生时金朝早已灭亡,尽管受父辈影响,偶而流露出一些“故国之思”,但毕竟不够遗民资格。对于南宋,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因此当元军大举攻宋时,会写出《渡江赋》这样的歌颂作品。[90]他出仕元朝,基本没有道义上的障碍,唯一形成约束的,就是“不如此(指拒仕)则道不尊”的崇道兼自尊观念。刘因别号“静修”(起初亦是斋名),来自诸葛亮“静以修身”一语,在诗文中也偶以诸葛亮自比,谓“太平自有诸公在,谁向南阳问孔明”。[91]可见他对政治的态度也有矛盾的一面,既想洁身自好,又希望像诸葛亮那样做一番事业。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祖望说他“盖知元之不足有为”多少有些绝对化,至少一开始并非如此。当然,把出处进退看作人生大事,对出仕时机的选择比较谨慎,这是刘因与当时其他士人不同的地方。时机在至元十九年似乎来临了。这一年权臣阿合马遇刺,朝政更新,元廷征召刘因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右赞善大夫是皇太子僚属,而皇太子真金又恰是朝中汉法派(包括汉族儒士和一部分汉化较深的蒙古、色目贵族)的旗帜和后台。刘因决定应召,一定是考虑到了上述因素。然而此次出仕却是浅尝辄止,昙花一现。没过多久,刘因就以继母生病为由“即日辞归”。此后他再未出仕,直到去世。
刘因甫出即退,固然有继母生病的具体理由,但毫无疑问他对这次短暂出仕的感觉很坏。《四皓二首》之二:
留侯在汉庭,四老在南山。不知髙祖意,但欲太子安。一读鸿鹄歌,令人心胆寒。髙飞横四海,牝鸡生羽翰。孺子诚可教,从容济时艰。平生无遗策,此举良可叹。出处今误我,惜哉不早还!何必赤松子,商洛非人间。[92]
这首诗借用商山四皓的故事,反思自己出仕之举,追悔之意十分明显。如我们所知,阿合马死后,汉法派并没有完全主控朝政,敛财派在忽必烈支持下,不久即卷土重来,朝中政争十分激烈。至元二十一年冬,阿合马党羽卢世荣进拜中书左丞,重新开展敛财工作。不久卢世荣被汉法派攻击倒台,下狱被杀,但与此同时皇太子真金与忽必烈的矛盾也更加激化,在谗言压力下忧惧而卒。刘因在短暂出仕期间,显然已经体验到了政局的险恶,因此才会有“一读鸿鹄歌,令人心胆寒”之句。他的激流勇退,必定与此有关。真金之死,使得朝中的汉法派官僚失去了靠山,也失去了与敛财派相抗衡的能力。[93]大约自此开始,刘因才真正“知元之不足有为”了。不仅如此,上引诗中“孺子诚可教,从容济时艰,平生无遗策,此举良可叹”诸句,似乎在暗示真金并不是“可教”的“孺子”。这与当时绝大多数汉族儒臣对真金的极口赞誉,截然不同。刘因何以有这种看法?我认为至少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东宫并未得到想像中的“尊师重道”礼遇。这方面有一些旁证。早在忽必烈即位之初,王文统为排挤姚枢、许衡、窦默三人,分别奏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之职。窦默准备接受任命,“欲因东宫以避祸”,但许衡反对说:“礼,师傅与太子位东西向,师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复此乎?不能,则师道自我而废也。”因此三人辞职不受。元武宗时,陕西隐士萧$被征为太子右谕德,到任不久,也力请去职,并对人解释原因称:“在礼,东宫东面,师傅西面,此礼今可行乎?”[94]虽然史无明言,但刘因一定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在蒙古贵族的观念里,所谓东宫官,包括师傅在内,不过是皇太子的一类怯薛“家臣”而已,首先要严主仆之分,而不重师生之礼。旨在“行道”的许衡,尚且不肯接受东宫职务;以道自尊的刘因,弃官而去就更不奇怪了。
九年后,即至元二十八年(1291),继阿合马、卢世荣之后的第三位敛财权臣桑哥倒台,“朝政又一更新”。[95]元廷复以嘉议大夫、集贤学士之职征召刘因,刘因致书宰相,辞不应征。这封信辞旨委婉,其中反复声明,不肯出山主要是因为身体欠佳,并非“有意于不仕”,自己也从未以“高人隐士”自居,希望宰相“俯加矜闵,曲为保全”。[96]刘因的态度引起了种种猜测。时任国子助教的吴明就上书认为,刘因拒绝征召,主要是对集贤学士的职务不满意,如果改授国子祭酒之职,付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的任务,则“庶有可起之理”,刘因必当“秣马膏车,待诏于保定北门之外”。元朝后期,杨俊民则说,假如真金在世,“嗣临大宝”,刘因又“天假以年”,早晚也会出山,“君臣都俞,道合言从,必能致王道之雍熙,还风俗之淳厚,俾儒者之效大白于天下”。[97]他们的分析似乎都简单了一些。我认为,刘因此次辞仕,是他理想主义人生态度与初次出仕挫折感受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态度是坚决的。身体欠佳固是事实(此后两年刘因就去世了),即使身体条件允许,也会找到其他的拒仕理由。联系到十三年前写的《退斋记》,他如果在已“退”后轻易复出,难道会没有“老氏之退”、“以术欺世”的嫌疑吗?自视甚高的他又如何向学生和世人交待呢?
中国古代不曾“忘世”的思想家,从来都很难在现实政治中找到充分“用世”的机会。在游牧民族建立的元王朝,儒家学者尤其会有生不逢时之感。生不逢时的悲哀,不仅在于无法“得君行道”,而且在于自己的出处进退往往不能得到时人和后人体谅。许衡在《退斋记》中受到的苛刻指责,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刘因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元朝后期有人提议以刘因从祀孔庙,终被搁置,反对者的主要理由,即认为刘因是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务独善者”[98]。而刘因的短暂出仕,又从相反角度受到了后代“遗民”的批评。清初大儒傅山被官府强行遣送入京,坚辞不肯受职,获得放还,对人说:“使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99]刘因如果在九泉之下听到上述评价,恐怕才会真正“死不暝目”吧!
【附注】
[1]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91《静修学案》引黄百家语,《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2册,第148页。
[2] 吴明:《荐刘先生充国子祭酒书》,刘因:《刘文靖公文集》卷27《附录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1a—4a页。
[3] 程钜夫:《雪楼集》卷21《故平阳路提举学校官陈先生墓碑》,阳湖陶氏涉园影印明洪武刊本,第9a—11b页。
[4]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4《内丘林先生墓碣铭》,陈高华、孟繁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23页。
[5] 刘因《示张源》诗:“堂髙余庆在,道重鲁斋传。洗眼名家后,惊心大学年。白头负风鉴,青佩见时贤。明日鹿门隐,须君拜我前。”这似乎是刘因著述中唯一正面提到许衡(鲁斋)的作品。此诗写作背景不详,具体内容也不完全清晰。见《刘文靖公文集》卷7,第4a页。
[6] 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徐子方:《挑战与抉择—元代文人心态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7] 见《刘文靖公文集》卷18,第5a—7a页。
[8] 见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28,四部丛刊本,第7a—9b页。
[9] 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四部丛刊本,卷31,第13a—14a页,卷33,第8b—9b页。
[10] 杜维明《刘因儒家隐逸主义解》。英文原文载Hok—lam Chen and Wm.Theodore de Bary (eds.),Yuan Thought: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 New York, G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汉译文见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钱文忠、盛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93页。杜维明猜测刘因的影射对象或许是刘秉忠,这绝不可能。刘秉忠固然是元初政坛中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其出处行藏“不见其迹”尤甚于许衡,但《退斋记》中有云“彼方以孔孟之时义、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刘秉忠断非以“程朱之名理”自居的人。
[11] 商聚德:《刘因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7—49页。
[12] 见《刘文靖公文集》卷27,第14a—17a页。
[13] 见《道园学古录》卷6,四部丛刊本,第3b—5a页;《国朝文类》卷35,第8b—11a页。
[14] 《国朝文类》卷30,第19b—20a页。
[15] 《道园学古录》卷36,第10a页。
[16] 许衡推动理学传播的功劳,在元代众口称誉,向无异辞。但关于他的学术造诣和个人作风,出自静修(刘因)、草庐(吴澄)两大门派的学者则偶有贬语,不过这种贬语通常是委婉或间接的。例如虞集在上引《南康路都昌县重修儒学记》中,正面称颂许衡一两句之后,话题一转说:“然而远域穷乡,执其书而无师友之辨,功利进取之士窃其绪余以干时,乐为简易之说者,而智不足以及其高明,姑窃其名以文其虚诞卤莽,而不可与入圣贤之域。”实际上就是在贬斥许衡及其学派。
[17] 见《刘文靖公文集》卷19,第4b—5a页。
[18] 关于《蠢斋说》一文及其影射对象,就管见所及,似乎只有近人许同莘曾予注意。他指出:“静修讥时人以椎鲁自号,盖即指鲁斋而言。”但未详加论证。见许同莘:《公牍学史》,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19] 见《刘文靖公文集》卷15,第1b页。
[20] 见《国朝文类》卷37,第16a—19b页。王旭作品今存《兰轩集》十六卷,系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但其中未收《上许鲁斋先生书》。
[21] 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7—248页。司马光也曾讨论过这个故事,指出齐王对孟子的态度是“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为名”,故而孟子“以为不义而不留也”。见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71《功名论》,四部从刊本,第1b—5b页。
[22] 许衡:《鲁斋遗书》卷9《与子师可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4a页。
[23] 没有证据表明王旭与刘因相识,但他们两人至少有共同的朋友。蓟州玉田(今属河北)人杨时煦(?—1271),字春卿,号庸斋,隐居教授,有名于时,元初官至兴文署丞。杨时煦是刘因的父执辈,与刘因虽未曾谋面,但对他十分关心。刘因与其子杨遇有交往,并在杨时煦卒后七年为撰《玉田杨先生哀辞》(见《刘文靖公文集》卷21,第13a—14b页)。王旭似乎与杨时煦的关系也不寻常,有五古《挽杨庸斋先生诗》、七律《挽杨庸斋先生》,见王旭:《兰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2,第13b—14a页,卷6,第2b—3a页。另外,忽必烈曾赐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真定藁城人王庆端(1225—1304)一根西域进贡的玉杖,刘因在去世前夕为撰《赐杖诗序》(《刘文靖公文集》卷17,第10b—11b页)。而“赐杖诗”的作者就包括王旭,见《兰轩集》卷9《御赐玉杖诗卷》,第17a页。
[24] 罗钦顺:《困知记》续卷上第六十六章,阎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5页。
[25] 见《明孝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影印本,卷147弘治十二年二月丁巳,第9b—10a页,卷151弘治十二年六月己丑,第1a—b页。有关此事始末,可参阅张德信:《明代科场案》,《明史研究》第7辑,合肥,黄山书社,第135—145页。
[26]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0《会试策问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a—b页。
[27]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2,盛冬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页。
[28]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32《列朝诸臣逸传·程敏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740页。
[29] 何乔新:《椒丘文集》卷30《赠特进左柱国太傅谥文庄丘公(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b—33b页)载:“公……弱冠著论,谓许文正公仕元,无能改于其俗,又不得信已之道,不仕可也。耆儒硕师见其论,初甚骇之,已而又大服,以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显然他们都没有读过刘因《退斋记》或王旭《上许鲁斋先生书》。
[30] 耶律有尚《许衡考岁略》(见《鲁斋遗书》卷13,第21b—32b页,以下简称《考岁略》)说许衡“建元以来,十被召旨,未尝不起”。这一说法不尽确切。忽必烈建元即位以后,许衡五次被召,又五度归隐,其出入时间皆明见于史料记载,并无“十被召旨”之多。“十被召旨”一说,应当是包括了忽必烈潜邸时期对许衡的几次征召(召为京兆教授、京兆提学等等)而言的。至元三年(1266)许衡第三次在朝期间,上奏疏《时务五事》(见《鲁斋遗书》卷7,第1a—16b页,又《国朝文类》卷13,第1a—17a页),其中说“以臣之不才,亦叨宠遇,自甲寅(1254)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诏旨”,可为佐证。
[31] 王磐:《鲁斋先生画像赞》,《国朝文类》卷18,第9b页。
[32]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9《元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赠正学垂宪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正许先生神道碑》(以下简称《许衡神道碑》),四部丛刊本,第1a—9b页。
[33] 《鲁斋遗书》卷14《先儒议论·薛文清公读书录》,第3b—4a页。
[34] 耶律有尚:《考岁略》。
[35] 见《鲁斋遗书》卷11,第13a页。
[36] 参阅陈高华:《论窦默》,《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116—125页。陈文形容许衡的送行诗说:“推崇之意,羡慕之心,溢于言表。”
[37] 参阅《鲁斋遗书》卷9《与子声义之》,第4b—5a页。
[38] 参阅《鲁斋遗书》卷9《辞免京兆提学状》,第1b页;同卷《与仲晦仲一》,第5b—6b页。
[39] 《元史》卷140《铁木儿塔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374页。
[40] 《元史》卷158《窦默传》,第3731—3732页。
[41] 《鲁斋遗书》卷7《时务五事》,第1a—16b页。
[42] 《鲁斋遗书》卷9《与窦先生》,第2a—3a页。
[43] “君臣遇合之契”是欧阳玄在《许衡神道碑》中的评论。明儒薛瑄则说:“世祖虽不能尽行鲁斋之道,然待之之心极诚,接之之礼极厚,自三代以下,道学君子,未有际遇之若此也。”就更加夸张失实了。见《鲁斋遗书》卷14《先儒议论·薛文清公读书录》,第5a页。
[44] 苏天爵曾记载:“初,世祖皇帝受封食邑于秦,至征大理,祃牙于斯。首聘鲁斋,见于六盘山下,命教授京兆子弟。”见《滋溪文稿》卷30《题鲁斋先生手书后》,第504页。据此在许衡出任教授之前,已获忽必烈召见。但此说十分可疑。耶律有尚《考岁略》未曾述及此事,相反却记载许衡出任教授前居于辉州(今河南辉县)苏门,为避教授之聘,还一度躲避到大名(今属河北)。如果他在此前曾远赴六盘山觐见忽必烈,《考岁略》失载如此大事,未免于理不通,而且许衡躲到大名避聘教授一事,也不好理解了。
[45] 耶律有尚:《考岁略》。
[46]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世祖嗜利黩武”条,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第429—430页。
[47] 姚大力指出:“对于传注之学与理学(它们都‘治经讲孔孟之道’)的区别,忽必烈也许从来不曾弄清楚过。”他将忽必烈对儒臣的使用归结为“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而超越学派观点的用人方针”,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见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7—224页。
[48] 见魏初:《青崖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a页。
[49] 见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b页。
[50]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7《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平章军国事行御史中丞领侍仪司事赠纯诚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鲁国公谥文贞康里公碑》,四部丛刊本,第16b—21b页。
[51] 李师圣:《汴梁泮宫修复石经记》,原载成化《河南总志》卷14、及光绪《祥符县志》卷20,转引自《全元文》第2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9—171页。
[52] 《鲁斋遗书》卷9《与张左丞》,第16a页。
[53] 《鲁斋遗书》卷5《中庸直解》,第17a页。
[54] 《鲁斋遗书》卷14《先儒议论·薛文清公读书录》,第3b页;同卷《郡人何塘表彰文正公碑记》,第22a页。
[55] 《元史》卷158《许衡传》,第3727页。
[56] 耶律有尚:《国学事迹》,《鲁斋遗书》卷13,第32b—35b页。
[57] 魏初:《青崖集》卷2《许左丞哀挽》,第22b页。
[58]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66《中书左丞许公真赞》,四部丛刊本,第24a—b页。
[59]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9,姚景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84页。
[60] 李谦《窦默墓志》记载:“上(忽必烈)即位,首召(窦默)至上都,问曰:‘朕尝命卿访求魏征等人,有诸乎?’对曰:‘许衡即其人也。’”。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内翰窦文正公》,第152页。
[61]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6,第3b—4b页。
[62] 商聚德:《刘因评传》,第48—49页。
[6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因曾写过这样的诗句:“纪录纷纷巳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见《刘文靖公文集》卷13《读史评》,第1a页。但他在《退斋记》中对许衡的讥刺,却完全是苛责“心术”、使人“受屈”的典型。
[64] 《鲁斋遗书》卷1《语录上》,第14a页。
[65] 除《退斋记》外,当代也有学者认为:“许衡在其个人的行为上却是以实践《老子》从而获益著名的,……他本身的历史哲学及天命观有时听起来像道家多于像儒家。”见柳存仁、朱狄·柏林《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三教》,载前接 Hok—lam Chen and Wm.Theodore de Bary (eds.),Yuan Thought: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汉译文见柳存仁:《道教史探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4—289页。
[66]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8《静修先生刘公墓表》(以下简称《刘因墓表》),第110—114页。
[67] 砚弥坚(1212—1289),字伯固,应城(今属湖北)人。被南伐蒙古军俘至北方,侨寓真定,教授为生,事迹见《滋溪文稿》卷7《元故国子司业砚公墓碑》,第106—109页。13世纪上半叶程朱理学在北方传播的关键人物赵复,就是同砚弥坚一起被俘虏到北方的。砚弥坚与理学传播应当也有一定的关系。
[68] 《刘文靖公文集》卷14《癸酉新居杂诗九首》之三,第2a页。癸酉为至元十年(1273),这一年刘因二十五岁。
[69] 《刘文靖公文集》卷23《希圣解》,第1a—3b页。
[70] 《鲁斋遗书》卷14《姚氏牧庵语》,第1a页。
[71] 耶律有尚:《考岁略》。
[72] 《元史》卷171《刘因传》,第4008页。
[73] 赵汸:《东山先生存稿》卷2《滋溪文稿序》,康熙二十年刊本,第33b—35a页。
[74]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0《真定安敬仲墓表》,四部丛刊本,第21b—23b页。
[75]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5《送李扩序》,第13b—16a页。
[76] 张养浩:《归田类稿》卷4《长山县庙学碑阴记》,乾隆五十五年刊本,第11a—12a页。
[77] 《宋元学案》卷91《静修学案》引黄百家语,第22册,第149页。
[78]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6《安敬仲文集序》,第3b—5a页。
[79] 吴宽:《匏翁家藏集》卷38《新安县重建静修书院记》,四部丛刊本,第17a—18b页。
[80] 《刘文靖公文集》卷19《书画像自警》,第8b页。
[81] 杨俊民:《静修先生祠堂记》。
[82] 《刘文靖公文集》卷11《次韵答石叔高》,第11a页。
[83]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征聘”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页。
[84] 这个故事出于虚构,早有学者指出。但近年出版的一些文学史、教育史著作,仍然不加说明地将它当作真实史料来使用,是不严谨的。
[85] 江存礼:《建言从祀》,《刘文靖公文集》卷27《附录上》,第20a—21a页。
[86] 崔铣:《洹词》卷9《休集》第61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b页。
[87] 《刘文靖公文集》卷1《冯瀛王吟诗台》,第9b—10a页。
[88] 苏天爵:《刘因墓表》。
[89]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3《书刘文靖公渡江赋后》,第9b—10b页。
[90] 《渡江赋》载于《刘文靖公文集》卷1,第5a—8b页。赋中指斥南宋为“蠢尔蛮荆”,为蒙古大军攻宋摇旗呐喊,誉为“应天顺人,有征无战”。此赋使刘因在后代(主要是明代)的形象大受影响。如周瑛《读刘静修渡江赋》云:“岂其居夷既久,虽有春秋之义而不知耶?或不欲以酸腐自居,而假此以彰其迹耶?”见周瑛:《翠渠摘稿》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8b—31a页。实际上金、元之际的北方士大夫普遍不重华夷之辨,而视南宋为僭伪,非独刘因为然。
[91] 《刘文靖公文集》卷11《次韵叩泮宫》,第12a页。
[92] 见《刘文靖公文集》卷2,第1a页。
[93] 参阅黄时鉴:《真金与元初政治》,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3—204页。
[94] 《元史》卷158《许衡传》,第3717—3718页;卷189《萧$传》,第4325—4326页。
[95] 苏天爵:《刘因墓表》。
[96] 《刘文靖公文集》卷22《与政府书》,第1a—2b页。
[97] 吴明:《荐刘先生充国子祭酒书》;杨俊民:《静修先生祠堂记》。
[98] 杨俊民:《静修先生祠堂记》。
[99]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6《阳曲傅先生事略》,第9a—12b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