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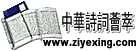 |
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 |
|
文/朱光宝 子夜星网站整理收录·仅供参考
上编·诗体流变
第三章 三言之衰
第一节 三言诗缘起与衰变
在中国诗歌体裁中,三言是一种没有得到发展的形式,因而极少有学者关注它的存在。但是在两汉时期,三言的乐府歌辞和谣谚铭文却在各类韵语体中占了不小的比重,魏晋乃至南朝诗人也偶有用这种体裁来抒情言志的。松浦友久先生在《中国诗歌原理》第五篇《诗与节奏》中曾专辟一小节讨论三言的节奏,认为以三字一句为意义表达单位过于短小,在重要的表达功能上缺乏畅达感,以此未能成为主要诗型。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18121页。这一基本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笔者所关注的是,三言能在汉代兴起,为何会衰竭于魏晋?三言与其他诗歌体式之间的流变关系又是如何?
两汉诗歌,以四言和骚体为主,然因表达需要,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等体式都已出现。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汉魏三言诗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存在于乐府郊庙歌辞,一类存在于民间歌谣谚语以及铭文中,文人诗极少。两汉三言的特征,首先在内容上绝大部分乐府三言以祝颂祀神和政治训诫为主,其原因可能与三言的来源和传统有关。《诗经》中少量以三言为主的诗主要用于赞美祝颂,汉代三言多赞颂,或许就是继承了《诗经》三言的这种特征。汉代郊祀歌用三言比例较高,可能和楚辞有关。楚辞中“三兮三”节奏是三言体的一个重要来源。楚辞的“三兮三”节奏,主要见于祭神曲《九歌》。汉代《郊祀歌》用去掉“兮”字就成为三言体的形式来祭祀神灵,就非常自然了。三言节奏短促有力,便于重复和记诵,这大概也是多训诫内容的汉诗好用三言的原因。至于民间歌谣谚语中纯粹用三言的都很短,通常只有四句,少的只有两句,多则六句。
汉代民间歌谣谚语大量出现三言,主要出自民间自发的讴歌。战国至秦代就出现了少量以三言为主的歌谣。秦汉歌谣偏重于对时事政治做褒贬评论,多针对一人一事作褒贬评论。三言谣谚因为简短,背景不明,往往用来影射、附会或预言某事。如汉代献帝时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用字谜暗示董卓之乱。又好用比兴,为便于传唱更重视押韵起兴,有时为凑韵而显得随意。因此,汉代三言歌谣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汉代铜镜铭文中也有一些三言,内容不外乎祝颂吉祥、企求富贵、祝愿延年、求仙长生;另也有一些表现相思的。不过,汉代三言极少抒情之作。
魏晋三言少于两汉,却也如后者一样,主要存于庙堂颂词和谣谚中。魏之郊庙歌辞有《太庙颂歌》其二为三言,鼓吹曲十二曲的标题大多根据汉曲而改,体式有的延续汉代同题曲,有的则不同,如魏之《楚之平》据汉《朱鹭》改,汉魏均为三言;魏之《战荥阳》为三言,据汉三三七式的《思悲翁》改;魏之《平关中》为三言,据汉之《将进酒》改,而汉原曲为杂言七言各一;魏之《克官渡》据汉三言《上之回》改,却是八句三言和九句四言加一句五言。吴之鼓吹曲十二首,也根据汉鼓吹曲改,使用三言情况与魏鼓吹曲近似,如《炎精缺》据《朱鹭》,全三言;《汉之季》据《思悲翁》,三言为主,杂以七言;《章洪德》据《将进酒》,全三言,等等。晋之郊庙歌辞和鼓吹曲辞多为傅玄所作,三言颇多,如《天郊享神歌》《地郊享神歌》各两首。鼓吹曲辞中的《灵之祥》据《朱鹭》,《宣受命》据《思悲翁》,《金灵运》据《君马黄》,全部为三言。张华作《食举东西厢乐诗》,第四、十、十一章均为三言;成公绥作《正旦大会行礼歌》十五章,第四、五、九、十、十一、十二章为全三言。从魏、吴、晋郊庙歌辞和鼓吹曲辞的沿革可以看出,其同异多是在三言和七言及三七言相杂的形式之间变化,这与三言、七言之间节奏的联系有关。西晋爱好雅音颂声,以四言为雅言之正;但是,郊庙歌辞却大量使用三言,可见他们不但认可三言适用于雅音,还进一步强化了三言的这一特性。
魏晋的杂歌谣辞中也有少量三言,也与汉代谣谚一样偏向于政治时事,多针对一事一人作褒贬评陟。魏杂歌谣辞均针对李庄、徐晃、陈群、陈泰,以及何、邓、丁、蒋、任氏而作。吴国歌谣除了评论李严、周瑜、司马氏以外,就是政权变易的谶语。晋时歌谣大多类似,或赞人物之政绩才能,或骂贾、裴、王三氏乱政。童谣也叙述了石勒、司马氏、庾氏等重要人物的兴衰。晋代文人所引的谚语,颇能以短句概括社会现象,如《晋书·鲁褒传》记鲁褒引谚语“钱无耳,可使鬼”;《初学记》卷二十《狱十一》录卫展陈谚言表说:“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有的谚语比喻也很生动,如《晋书·赵王伦传》载时人评赵王伦的谚语“貂不足,狗尾续”,此语后来变成了成语。由是可知,魏晋三言谣谚在内容功能乃至篇幅上,继承并保持着汉代的基本特点,只是数量越来越少,渐至湮没。
魏晋文人三言寥寥无几。西晋傅玄对三言的把握较为娴熟,写过许多三言郊庙歌辞,但抒情诗仅一首《车遥遥篇》,以“三兮三”的骚体句和三言相杂,还有一首题作《杂言诗》的纯三言,都是短篇。傅玄如此熟悉三言,以三言抒情也只是偶一为之,可见此体不易掌握。南朝鲍照写出《春日行》,为文人三言中仅有的一首成功的长篇抒情诗。
三言诗歌发端于先秦,兴起于汉,衰于魏晋,上文已将这一过程较为清晰地呈现。三言体在汉代兴起却在魏晋以后逐渐衰落的原因,将是下文我们考察的重点。
第二节 三言衰变探源
将魏晋三言体和汉代三言体做一比较,会发现从内容和功能上看,魏晋三言基本分别走着大雅和大俗的两条相反道路。所谓大雅,是指按着古乐府题目的体裁传统在乐府的郊庙、鼓吹、舞乐中传承下来。汉代三言乐府本有极少数反映了民间思想感情的篇章,魏晋则清一色歌颂庙堂的雅音。大俗是指民间按其固有的表现方式刺时评人,题材内容愈趋萎缩。雅俗两条路径的内容功能完全相反,而没有交会点。此外,三言的传统功能没有给文人留下自由抒情的空间,因此即使有民间歌谣和其他韵语的土壤,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当然,三言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本身的局限。三言的特质是因声成节。三言句的节奏构成,除了极少数例外,基本上摒弃了虚字和“兮”字的成分,完全由实词构成语法意义完整的句子。因为是每句只有三个实字的固定句型,三言只有两种构句方式:一个双音节词加一个单音节词,或三个单音节词。在《诗经》和《楚辞》里,这样的构成只是句子成分。诗经体四言中,必须加“兮”字形成二二节奏;楚辞体里,在两个三言之间或一个三言和一个二言词组之间加“兮”构成基本节奏音组。而三言在独立成句以后,其基本节奏音组自然随之确立,它的两种构句方式在意义节奏上虽有区别,但诵读的声节都只能是一句三拍。读起来节拍感很强,便于在快节奏中记诵,所以最易为民谣儿歌所接受,《三字经》长期以来用作儿童启蒙教育,并流传至今,正是基于这一道理。
三言句构成诗行,也应具备押韵和章节的基本单元这两个要素。三言歌谣在民间传唱,为了顺口很容易调整韵脚。所以,三言歌谣找到了自己的押韵规律,大体有句句押韵、隔句押韵两种,且基本上以两句为一单元或四句为一单元。而乐府歌辞中较长篇的三言押韵就较为复杂,有的一韵到底,如鼓吹曲辞中的《将进酒》;有的隔句押韵,每四句换韵,如《天马》,具有以四句为一单元的意识;有的不押韵,如《安世房中歌》其七;更多的长篇都是隔句韵,如《郊祀歌》中的几首三言。由此可知,三言与四言五言的押韵方式和章节基本单元大体相同,显示出汉人建构三言体的自觉意识。
三言体的产生有两个不同的来源:歌谣类语言直白朴拙,应出自民间口语;郊庙、鼓吹、歌辞三言篇幅较长,构句保留着楚辞三言词组的特点,当是来自楚辞体。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引太宰嚭遣大夫种之言:“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这是战国韵语中常用的“三×三”的句式,亦多见于楚辞。《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引此语说:“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有所变化,但可以看出二者的渊源关系。《史记·乐书》载有一首汉武帝《西极天马歌》:“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其中三言和“三兮三”的骚体句混用;《汉书·燕刺王旦传》载燕王刘旦《歌》首句:“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都很容易看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骚体中的“三兮三”节奏,大部分可以去掉“兮”字独立成三言句,如《九歌·国殇》中的“操吴戈兮被犀甲”,《山鬼》中的“被薜荔兮带女萝”,等等。但《山鬼》中的“岁既晏兮孰华予”,《国殇》中的“诚既勇兮又以武”,这一类也或由于意义直贯全句,或由于倒装或使动句式,变成三言会显得生涩。汉代三言多受到楚辞这类三言词组构成的影响,《郊祀歌》中的《练时日》中有“灵之来,神哉沛”,而汉武帝《瓠子歌》有“归旧川兮神哉沛”,“神哉沛”的结构显然是适宜于骚体而不宜于独立成句的。文人作的三言也因来自楚辞体而有构句生硬之病,如前引刘旦《歌》二首,其一中“背尊章,嫖以忽;谋屈奇,起自绝”这类句子,显然是楚辞体三言词组的特点,如果在每两句三言中加上“兮”字,显然要顺畅得多。
分析了三言的节奏结构和诗行、体制,可以看出汉人好用三言,很可能是因为这种节奏最简单,容易掌握,不像四言和骚体那样需要寻找主导的节奏音组,也不像五言那样因为句式增加了两个字便不容易找到节奏感,而且无论长短都可以成体,既可以运用对偶、排比、重叠等促使诗行节奏流畅的修辞手法,又不必像诗经体四言和早期五言那样依赖它们构成句序。
魏晋时期,三言不能获得长足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三言体不适宜抒情。从体式原理来看:
首先,三言的诵读节奏过于短促单调,不能表现抒情所需要的长短曲折富有变化的声情。三言一句三拍,由三个均等的单音节组成,节拍感虽然强烈,但诵读时缺乏轻重长短的调节。乐府中的三言郊庙歌辞、鼓吹曲辞如果配乐,慢声歌唱可能会淡化短句节奏之间的顿断感,但是文人抒情诗主要用诵读节奏,而在两个三言词组中间加上“兮”字的骚体句,则可以因“兮”字的感叹语调延长两个三言句之间的节拍。试看汉代以“三兮三”节奏为主的骚体,如枚乘、司马相如、李陵、张衡的《歌》,汉武帝的《秋风辞》《瓠子歌》,都具有浓重的抒情意味。而崔骃的三言诗“屏九皋,咏典文,被五素,耽三坟”只是像说教。李尤的《武功歌》仅存片断“鸣金鼓,马模起,士激怒”,也可看出三言与歌颂武功的铿锵节奏正相配合。对于三言和骚体节奏感的这种区别,魏晋诗人似乎已经觉察,石崇的《思妇引》基本上是三言,仅杂八言一句,七言三句,序文说“此曲有弦无歌,今为作歌辞以述余怀”。三言作为歌辞,有弦乐相配,其歌唱节奏或许不会影响述怀,而他又另作一首《思妇叹》,则是全篇“三兮三”的骚体诗。同样的内容,作为不歌的诗,用骚体更为适宜,这应该是石崇区分两种诗体的理由。魏晋文人三言抒情诗成功的作品极少,仅可举出傅玄《杂言诗》“雷隐隐,感妾心,倾耳听,非车音”,思妇误以雷声为车声,“雷隐隐,感妾心”,在等待的专注和痴迷中听声音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原来那不是归人,只是过客。此诗最大限度发挥了三言体便于由小见大的含蓄特性,但这种构思角度对于长篇便有较大的局限性。晋苏伯玉妻的《盘中诗》有四十二句三言,写思妇盼望丈夫归来的哀怨,但与相同内容的古诗十九首之《明月何皎皎》相比,就显得过于直白急促,缺乏委婉回环的韵味。
三言抒情长篇的佳作,当推刘宋鲍照的《春日行》:
献岁发,吾将行;春山茂,春日明;园中鸟,多嘉声;梅始发,柳始青;泛舟舻,齐棹惊;奏采菱,歌鹿鸣;风微起,波微生;弦亦发,酒亦倾;入莲池,折桂枝;芳袖动,芬叶披;两相思,两不知。〔见(宋)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卷六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全诗语言明快,使用了三言谣谚中常见的排偶句式,重复用字,这就使三言句短促的单字节奏因重叠而得以延缓,增加了骀荡的声情,尤其是此诗前半写一路游春观景,后半写水上嬉游的情景,三言短拍的分明节奏和轻快的脚步以及齐棹划桨的节奏感取得一种照应,更巧妙地发挥了三言体式的长处。但巧思难再得,这正说明了三言体难以在抒情方面发展的原因。
其次,三言构句太简单,在艰涩与直白之间难以取其中,郊庙歌辞和鼓吹曲辞的难解,相当程度上与三言构句的古奥生涩有关。正如《史记·乐书》所言:“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郊祀歌》十九章的文辞连通一经之士都不能明白,必须五经会讲,可见其中用了多少经书尔雅之文。鼓吹曲辞也同样如此,如《将进酒》用了《大招》和《周礼》的内容,先秦经书中的四言句和散文句要压缩入三言句,必然会产生为文造词的问题,这就更加难懂。另一方面,民间三言歌谣虽然语言朴拙通俗,但也同样有许多难解之处,主要是因为两句或四句一单元的简短形式无法容纳背景的说明,如《后汉书·单超传》载天下为徐、具、左、唐四侯语“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东观汉记》载马太后引俗语“时无赭,浇黄土”之类。尤其是影射附会的谣言俚语,即使看懂字面也无法解释,如《汉书·翟方进传》引汝南鸿隙陂童谣“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葵。近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之类。至于镜铭中三言硬凑的例子更多。这说明汉魏三言的两种主要类型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古雅和通俗口语之间不容易找到一种适中而易于普及的诗歌语言。
三言体在汉代兴起,是民间口语的发展和骚体节奏自然演变的结果。但是三言这种诗体在节奏和构句上的局限性,导致其难以适应抒情诗对感情表现和节奏变化的多种要求。而在中国诗歌的传统中,不便于抒情的体式终将被淘汰。这是纯粹的三言体生命力不能持久的根本原因。但是以三言节奏为主导的三三七体,却因突破了三言的局限而发展成一种节奏固定的杂言诗体,在七言的生成过程中起过促进作用。
〔共八页〕
1
2
3
4
5
6
7
8
上一页 下一页
|